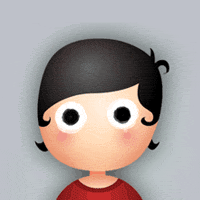“路内的小说是一代人的精神镜像。他笔下的青春,不仅是年华,也是灿烂的心事,不仅常常受伤,也饱含生命的觉悟。”
路内,1973年生,被称为最好的七零后小说家之一,著有“追随三部曲”(《少年巴比伦》《追随她的旅程》《天使坠落在哪里》)以及《云中人》《花街往事》。4月16日,路内凭借最新作品《慈悲》,被授予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。
对于《慈悲》,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评价其“见证了一个作家的成熟和从容。从伤怀到悲悯,从锋利走向宽阔,路内的写作已不限于个人省思,而开始转向对平凡人生的礼赞,对日常生活肌理的微妙刻写”。
▼
4月25日,读者新媒体邀请作家路内做客“读者·乐读会”,在微信群做直播访谈,和读者畅谈他的新书《慈悲》,分享他的写作与思考。以下是活动的文字记录。
《读者》:《慈悲》似乎和您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样,很多人说第一次看到这本小说的时候很震惊,都怀疑跟写“追随三部曲”的是不是同一个作家。这种转变是有意的吗?
路内:写《追随她的旅程》、《少年巴比伦》的时候,我三十多岁,可能三十多岁的时候,人的心态还是很年轻的。但是现在我觉得,过了四十岁写的长篇小说肯定会和以前有些不一样。这是自然的,可能也是不自然的。“不自然”,可能是有个文学的自我意识。“自然的”,就是因为年纪大了。当然,我不排除也有返老还童的机会,呵呵。
《读者》:很多人说《慈悲》像余华的《活着》,题材上也类似,都写到了饥荒,写了上个世纪下半叶的普通人的生活。您怎么看这种类比?
路内:这个类比蛮有意思的,因为作家本身有上下文的关系。但我恐怕不宜过度讨论余华老师的作品,尤其是余华老师的小说非常优秀,有很高的价值。其实往上看的话,在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身上,可以看到很多当代作家、现代作家,包括外国作家的影子。有时候,我觉得《慈悲》这个小说其实有些像鲁迅的痕迹。这种上下文的关系,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传承的关系吧。
补充一点,坊间有时候说像《活着》,其实我有一点点自己的疑惑。我觉得至少在视角上就不太一样,《活着》是第一人称的视角。对写小说的人来讲,视角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关系到一个小说的语调、节奏等等。
《读者》:《活着》写苦难有种温暖的底色,让人感动得稀里哗啦,同时又像从文中伸出一只手来拥抱人的感觉,给人慰藉。《慈悲》的视角很客观,似乎只是把苦难呈现给我们,令人悲从中来,然后就不管了。您怎么看这种观点?
路内:对,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说的技术问题。就是说,小说家在取一个视角的时候,一个什么样的写法的时候,其实他已经很深刻地考量过。如果一定要再谈余华的话,。。你看鲁迅写《阿Q正传》的时候,也都是那样一种眼光。从现代文学的源流上讲的话,其实大家都非常接近。
《读者》:《慈悲》里的生活很沉重,所有人好像都在一个小小的蚕茧里挣扎缠斗,找不到出路,看了让人很绝望很难受,好像我们只能这样卑微无助地活着。小说最后借水生弟弟之口,有了唯有慈悲的领悟,这是您给他们的出路吗?
路内:不是,这个小说哪有什么出路!我觉得所有出路都在历史现实中间。作家不会故意给人物制造这样一种出路的。所有的人物都是走向当代,走向今天,走向我们的现在。小说结尾是一个寓言式的结尾,其实并不是为了让人物获得一个什么救赎。
《读者》:《慈悲》这个书名用的是佛语。小说里也多次写到了生死,水生的父母、师傅、叔叔、妻子,最终都凄凉地死去。有个片段,玉生病重后说,人都是要死的,小何医生却说,你讲错了,人都是挣扎着活下来的。生与死似乎是您的小说主题。您是怎么看的?
路内:这部小说谈论的很多就是中国人很普通的生死观念。至于这个词是不是来自,甚至来自,并不是特别重要。其实无非是借用了一下或其他宗教的用词,最终要表达的还是一个很普通的理念。它是一个文学理念,不是一个宗教理念——也不能说文学理念普通。
《读者》:您作为70后作家,是比较年轻的作家,为什么关注的是对大家来说已经过去的事,而不是更当下的生活状态?比如当下城市里的普通人的生活?
路内:对,你讲得非常有意思。但我已经不算很年轻,我1973年生的,是比较老的那辈70后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作家的想法有关系,尤其是对于写长篇小说的人。我八年写了六个长篇,我似乎有一种故事没写完的感觉。但是,我也在放弃很多故事,慢慢把注意力放在更值得讲的故事上。四十岁以后我觉得还是少写一点比较好,哈哈。
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,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。如果我十年只能写一个长篇的话,我会写哪一个题材。这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。
《读者》:《慈悲》的时间跨度非常大,很多情节也有历史背景,但您似乎有意避开历史事件,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两句。这和大多数作家的写法很不一样,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?
路内:这是一个技术考量问题。既然一个小说,你用的语调什么的,各方面都很简单、简洁的话,就不宜过多考量历史节点上的一个一个事件。因为考量历史节点,无疑会导致整个小说非常臃肿。因为你必须去写细节,必须把事件对人造成的具体的、不同的影响写出来。但是我觉得这么写的话,没什么意思。其实我在写《花街往事》的时候已经尝试过这种方法,对此我已经没什么兴趣。
然后,采用这种简洁的、模糊历史的写法,本身也是有寓意的吧。它能表达出我的一种观念。其实这在小说写作上也是有其合法性的。海明威不是有冰山理论嘛,他说最重要的那些东西,十分之九都在海面以下,只有十分之一在海面上。我觉得那些密度啊、体积啊,更大的东西其实都在那些没有诉诸文字的内容当中。
《读者》:小说中最让人感觉温暖的就是复生这个人物。土根望着复生穿着红衣服在山上跑步的时候,忍不住感慨:“水生,我们都白活了啊。强生和她比起来,就像一头猪啊。”不仅如此,小说里所有人和她相比,都显得晦暗无关。刚好她的名字也是死而复生的意思。您对这个人物是不是有特别的寄托?
路内:有吧,她无疑代表了首先是我对小说里面人物自身命运的寄托。原来小说里的人物都活得很惨,关键是活得没什么希望。我觉得至少年轻一代人是有点希望的。但是我写完以后一看,其实复生跟我的年纪差不多,她要是真实存在的话,现在也该四十多岁了,其实也没什么大的希望,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挺扯淡的。但在小说里,她至少是个年轻人嘛。
《读者》:小说后面水生帮浙江一个工厂画图纸,试车成功的时候,他感叹,他终于搞垮了自己的厂。令人忍不住感慨。这是不是一种隐喻?
路内:我觉得算是一种隐喻吧,其实是一种很明确的比喻。你看这个故事讲的是90年代后期深化改革的结果。其实它不是个人选择的报复,而是历史变迁的结果。当时,他们的工厂在整个体系中崩溃,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觉得,它不完全是一种比喻。可能是比喻,可能也是现实和事实之一。这种整体的经济变化,对全世界的老百姓的影响都非常大。生活方式的改变、观念的改变,其实都是基于这个。
《读者》:您的小说有种真实的质感,很多细节都让人愿意相信是真实发生的而非虚构的。您的写作中有多少是自己的经历?怎么处理现实与虚构?马尔克斯说,一个作家是写自己经历的事,还是写听来或读来的事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您怎么看?
路内:我以前觉得马尔克斯说话挺好的,很重要。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。但是后来,我觉得这对小说家其实不重要。如果你永远只写自己身上发生的事,那你整个的局限性会非常大。小说退回到个人的话,那对作家的内心会有一个巨大的考量。就是你内心到底有多大。很多人内心没有这个世界大,只有少数人的内心比这个世界深邃。这是每个人天分的不同。我觉得在取材的时候,是虚构还是个人经验,其实不重要。因为小说终究是一个虚构的艺术。
小说作为一个虚构的艺术,存在的一个问题是,你即使在写自我、自身的经验的时候,在美学上仍然是假的东西。只要你呈现出这样一个作者视角,通过叙述人的口吻去写的话,它就是假的,它就是虚构的。说错了,虚构不等于假,虚构并不等于不真实,虚构仍然可以是真实的,真实的对面是假。事实上,这种虚构的写法往往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,有时候甚至比报告文学的力量更强大一些。
这一点你去看电影就知道了。一个真实的记录片,在电影院里面讲述的效果,或者说梦的效果,总是会比真正的故事片、剧情片稍微差一些。因为剧情片有它的营造法,有它的往上传承的巨大源流。
所以你看人类文学的传统,往上追溯,最早就是《》《荷马史诗》这些,全是虚构作品。其实从古埃及时代传下来的真实的资料也有,象形文字也被解读出来了,但是那个东西没什么意思,它没什么文学的力量。我觉得文学的力量就呈现在这个角度上。因此你去判别什么东西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,其实没什么意义。你看到一个文学作品,觉得它很真实的话,其实它只是虚构得特别好。
《读者》:您最近有哪些写作计划?
路内:今年事挺多的。先要把“追随三部曲”的一个番外短篇小说集出版了。差了一些没写完,大概还有一半的工作量。其实那些小说我都没来得及写。同时还在写一部写了一年的长篇小说。小说时间跨度很漫长,写两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年经历。
▼
听众提问:这部小说的名字是《慈悲》,这个慈悲是不是佛学概念?
路内:这个所谓慈悲是不是佛学概念,小说里面其实提到了,去参神拜佛,但是小说标题里面的慈悲,和的慈悲还是有一点差别的。至少它谈到了一种反向的东西,比如国家对人的一种慈悲心理,这个慈悲心理究竟是可喜的、可悲的,还是可怕的,是值得讨论的。但是作为作者过多地解读这种东西,不太像一件正经事。我觉得我还是谈谈小说是怎么写的比较好玩。
听众提问:小说把工人的生活写得很细致深入,您自己是不是也有过当工人的经历?
路内:我确实是有过这样的经历,当了四年的工人。那是我很年轻的时候,家里很穷,就得去厂里上班,我母亲那时候也很伤感,没钱供我读大学。那是在90年代初,非常遥远的事情。我的家庭背景是非常普通的家庭,我父亲是工程师,我母亲是工人。这样的背景给了我很多写作的素材,我太熟悉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讲话的方式了。
听众提问:《慈悲》是一部悲剧小说吗?
路内:我觉得《慈悲》并不属于悲剧小说,事实上小说门类中也没有悲剧小说、喜剧小说的区分。这不算一种分类。除了诙谐类的,其他都是偏向悲剧的。甚至有些喜剧类小说,其实最后仍然是悲剧。因为它的指向性是一样。小说家会用一种反讽的手法,一种非常快乐的手法,让你感受到生活极其残忍的一面。
听众提问:您在写《慈悲》的时候是伤感的还是平静的?
路内:我有时候会很伤感。因为我会被小说本身带进去。我有时候也会想,这种伤感是不是很庸俗。我也在慢慢地让自己隔离开,能够带着一种相对更远的距离去看我小说中的人物。但有时候还是免不了会伤感,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。
听众提问: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?
路内:我比较喜欢的作家,过去比较喜欢卡夫卡、福克纳、马尔克斯,最近几年喜欢博拉尼奥,然后通过朋友私底下的翻译,慢慢喜欢上一个作品还没有被翻译到中国的作家,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,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作家。
听众提问:从《慈悲》开始,您的创作是不是从青春文学转向严肃文学?
路内:其实我不觉得我以前写的是青春文学,当然有人愿意这么说我也无所谓。我也不觉得此后就走向了文学界所说的严肃文学。因为我觉得文学本身有一些“不严肃”的东西。写一部小说的时候,我会用各种手段,比如反讽,用各种视角去处理我要的各种题材。其实我过去的青春叙事里面,已经包含了我要讲的这些东西,只是评论界没有看出来。但我觉得中国评论界还是有很多人看出来了,我以前的小说也有很多文本分析的东西。
听众提问:您觉得在当代中国做一个职业作家现实吗?要写出伟大的作品,必须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吗?
路内:把作家当成一个职业是非常具有现实感的事情,它会让作家保证一定的产量、一定的质量。但是这件事对写出第一流的作品,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它似乎可以保证写出三流以上、一流以下,这种中等偏上的作品,这是可以保证的。作为一个职业的话——职业嘛总有职业的取向性,但是文学有文学的另一种取向性。
▼
获得路内签名版《慈悲》的幸运读者:
火火、薇薇、兰州妹子、慧慧、花影、camille、韩新玲、静水流深、槐树下、琛琛
恭喜10位幸运读者,也感谢每一位参与活动的读者,期待各位再来参加下一期的读者·乐读会,与你们喜爱的作家互动交流。
编辑:陆禾
“读者·乐读会”是读者新媒体全新上线的访谈栏目,我们将不定时邀请著名作家、学者及各领域嘉宾,做客读者在线访谈,和读者分享知识与经验。欢迎你的关注和参与。
▼
4月20日读者×豆瓣阅读《你在北京还好吗》赠书活动的幸运读者:
流离公子(辽宁)、苗&籽—(广东)、瑶贝希(湖南)、miku(陕西)、夏雨天(江西)、夏叔叔(重庆)、A-哈哲尔(四川)、约定◉‿◉(挪威)、背包客(广东)、阿瑾(阿尔巴尼亚)
请以上10位读者在文末留言,留下联系方式和电话,我们将尽快把书寄给你。